
2015年8月,郭憲光在新疆調(diào)查沙蜥。受訪者供圖
1995年的畢業(yè)季,22歲的郭憲光完成了本科畢業(yè)論文,研究對象是蘭州皋蘭山上的密點(diǎn)麻蜥。那時(shí),由于采樣范圍有限,分析并不深入。
2006年,33歲的郭憲光主持了自己的第一個(gè)科研項(xiàng)目“中國麻蜥屬的系統(tǒng)分類研究”。
看到“麻蜥”二字,他感慨萬千。兜兜轉(zhuǎn)轉(zhuǎn),終于回到“原點(diǎn)”。
現(xiàn)為中國科學(xué)院成都生物研究所(以下簡稱成都生物所)副研究員的郭憲光,18年里,常穿梭于中亞干旱、荒涼的地方,尋找那些隱藏在黃沙和土礫中的精靈——麻蜥和沙蜥。他給自己取了個(gè)網(wǎng)名——走過荒漠。
回到起點(diǎn)?走過荒漠
本科畢業(yè)后,郭憲光離開蘭州大學(xué),成為河北農(nóng)業(yè)技術(shù)師范學(xué)院(現(xiàn)更名為河北科技師范學(xué)院)動物科學(xué)系的一名助教。因掛念父母,兩年后他回到家鄉(xiāng)四川,成為了一名監(jiān)獄民警。
步入千禧年,出于對動物學(xué)研究的熱愛,他決心繼續(xù)深造,攻讀碩士和博士學(xué)位。讀博期間,郭憲光在中國科學(xué)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攻讀水生生物學(xué),主要研究魚類分類與進(jìn)化。
他對分子系統(tǒng)學(xué)等研究方法的運(yùn)用非常熟練,就算“跨界”研究其他動物也并非難事。正因如此,臨近博士畢業(yè)時(shí),郭憲光收到了成都生物所兩棲爬行動物研究室的邀請。
2006年,加入成都生物所后,郭憲光除了主持研究項(xiàng)目,還基于前輩關(guān)于中國沙蜥演化歷史的論文,運(yùn)用多種方法重新分析了沙蜥的時(shí)空演化歷史,以及與青藏高原隆升和西部荒漠化的關(guān)系,并撰寫發(fā)表了論文。
這篇論文讓他意識到,如果沒有豐富的野外科考經(jīng)驗(yàn)作為基礎(chǔ),研究兩棲爬行動物將變得非常“抽象”。“在此之前,我都沒有真正涉足荒野,本科時(shí)也只在皋蘭山上進(jìn)行過簡單考察。”
自2007年起,郭憲光便立志“走過荒漠”,麻蜥和沙蜥是研究重點(diǎn)。
這兩類爬行動物是中亞干旱荒漠區(qū)的代表性物種,麻蜥的分布范圍從歐洲的羅馬尼亞一直延伸到亞洲的朝鮮半島,沙蜥則跨越歐洲東南部及其鄰近的亞洲西部和中部地區(qū)。在中國,麻蜥屬和沙蜥屬的物種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區(qū)的荒漠和草原地帶。
因此,郭憲光的科考足跡遍布亞歐大陸,西起高加索和里海,東至蒙古,北達(dá)貝加爾湖。每年,他都會投入一個(gè)多月時(shí)間,深入國內(nèi)西北地區(qū),進(jìn)行詳盡的本底資源調(diào)查。
他是迄今為止唯一 一位到達(dá)里海和咸海進(jìn)行兩棲爬行動物調(diào)查研究的中國學(xué)者。
在野外,郭憲光和團(tuán)隊(duì)每天都要奔波幾百公里,調(diào)查七八個(gè)樣點(diǎn),常常從早上七點(diǎn)工作到深夜。生活在干旱地區(qū)的蜥蜴,其膚色與環(huán)境顏色極為接近,具有隱蔽性。因此這項(xiàng)工作很費(fèi)鞋,他們不僅要一邊走一邊用木棍輕敲地面,還要用腳踹那些容易扎手的灌叢,“逼迫”這些小精靈現(xiàn)身。
根據(jù)以往的研究報(bào)道,有些種類的蜥蜴在晴天比較活躍,有些則害怕高溫,甚至在六七月有夏眠的習(xí)慣。“我們必須仔細(xì)搜查,了解它們的活動規(guī)律,再根據(jù)這些規(guī)律去驗(yàn)證和尋找。”郭憲光說。
蜥蜴見證的滄海桑田
“自19世紀(jì)以來,許多國外學(xué)者,尤其是俄羅斯學(xué)者,對中國干旱荒漠區(qū)進(jìn)行了區(qū)系調(diào)查和新種命名,因此很多物種資料都掌握在外國人手中。”在國內(nèi)動物志編撰過程中,郭憲光發(fā)現(xiàn),現(xiàn)有一些相關(guān)信息存在錯(cuò)誤或遺漏,亟待澄清,“但模式標(biāo)本大多保存于國外”。
首先做好本國的生物資源研究是郭憲光的心愿。除了野外考察,他多次前往俄羅斯科學(xué)院動物研究所,查閱麻蜥和沙蜥的相關(guān)標(biāo)本與文獻(xiàn)。
郭憲光的研究,不只是采集和研究標(biāo)本、了解物種分類特征。亞洲中部干旱區(qū)的形成與演化,是第三紀(jì)以來最重要的地質(zhì)歷史事件之一,被認(rèn)為與青藏高原隆升、全球氣候變冷、副特提斯海退卻等密切相關(guān)。
干旱荒漠區(qū)占據(jù)了中亞內(nèi)陸干旱區(qū)大部分。“探討這一區(qū)域氣候環(huán)境變化對生物多樣性形成與演化的影響,意義重大。”郭憲光表示,沙蜥和麻蜥已在中亞干旱荒漠區(qū)生存了數(shù)十萬,甚至數(shù)百萬年。它們對氣候變化響應(yīng)敏感,物種分布和演化過程見證了這一區(qū)域的滄海桑田。
“想要獲得對中亞干旱區(qū)全貌的認(rèn)識,就不能止步于中國境內(nèi)西北干旱荒漠區(qū)的研究,必須向西、向北拓展。”因此,郭憲光更加注重國際合作和交流。
2023年,郭憲光與哈薩克斯坦動物所的研究人員合作,追溯旱地沙蜥的起源。他們對旱地沙蜥的現(xiàn)存分布區(qū)進(jìn)行全面調(diào)查,收集了96個(gè)種群共300號個(gè)體信息,并利用2個(gè)線粒體基因,構(gòu)建其譜系地理結(jié)構(gòu)。同時(shí),對其中27個(gè)種群的51號個(gè)體開展簡化基因組測序。
最終,郭憲光找到了旱地沙蜥的“祖籍”——費(fèi)爾干納谷地,并對照區(qū)域地質(zhì)演化時(shí)間,發(fā)現(xiàn)在晚上新世時(shí)期,隨著中亞干旱化的加劇,這個(gè)族群快速輻射。到了更新世時(shí)期,盡管冰川循環(huán)造成高緯度地區(qū)種群滅絕,但中亞干旱區(qū)反倒提供了避難所,成為種群交流的重要走廊。
有辛苦,有驚險(xiǎn),有熱愛
郭憲光說,如果內(nèi)心沒有熱情,日復(fù)一日的野外跋涉是不可能長久堅(jiān)持的。
考察中,危險(xiǎn)時(shí)有發(fā)生。2015年6月,郭憲光及其團(tuán)隊(duì)到達(dá)了哈薩克斯坦伊犁河谷下游。一天下午,他們在一片平地上扎營。帳篷剛剛搭好,狂風(fēng)暴雨突襲。大約一個(gè)小時(shí)后,雨勢漸歇,但隨之而來的是一陣寒意。郭憲光下車取下背包,正準(zhǔn)備穿上沖鋒衣時(shí),隨隊(duì)的司機(jī)突然沖過來,一把將他拽進(jìn)車?yán)铩?/p>
郭憲光還沒來得及反應(yīng),司機(jī)已經(jīng)跳上車迅速掉轉(zhuǎn)了車頭,向地勢高的地方疾馳而去。透過車窗,他們看到,剛才營地旁平靜的小溪,已經(jīng)變成洶涌的洪流,瞬間將那些來不及收走的帳篷和睡袋卷走了。
科考路上雖然有辛苦、有驚險(xiǎn),但沿路的人文歷史和地理風(fēng)貌成了他的慰藉。每次踏上河西走廊,雖然眼前是一片生機(jī)難覓的大漠,但郭憲光腦海中卻能浮現(xiàn)出2000多年前霍去病鐵騎建功的場景。
這些所見所想讓郭憲光感慨萬千:隨著時(shí)間流逝,許多往事已成塵埃,只有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數(shù)百萬年的蜥蜴,成了忠實(shí)的見證者。
他還想去看更多風(fēng)景,探尋更多未知。近日,郭憲光申請的一個(gè)中亞國際合作項(xiàng)目已經(jīng)獲批。“土庫曼斯坦、吉爾吉斯斯坦這兩個(gè)地方,我還未曾踏足。未來3年,我想走遍整個(gè)中亞。”
(原載于《中國科學(xué)報(bào)》?2024-12-26?第3版?綜合)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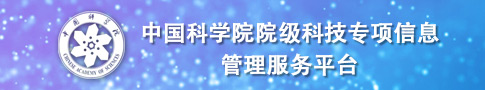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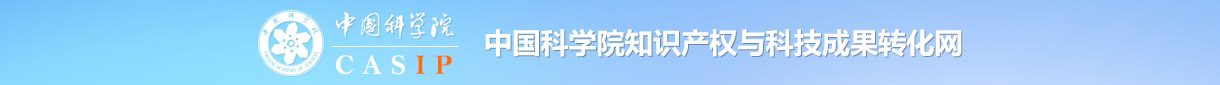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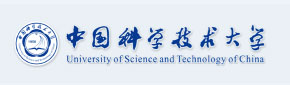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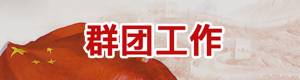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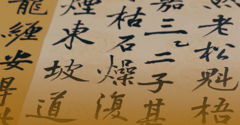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 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402500047號 網(wǎng)站標(biāo)識碼bm48000002
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402500047號 網(wǎng)站標(biāo)識碼bm48000002
